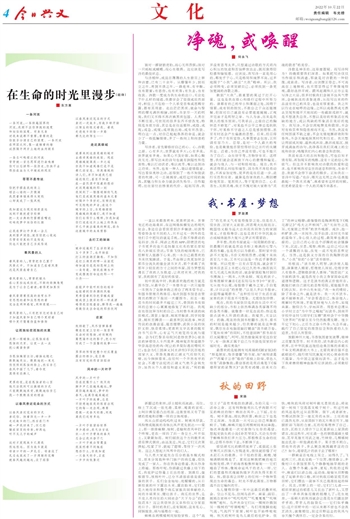罗迦勇
一直以来都喜欢书,更喜欢读书。世事变迁的沧海桑田,在这网络纵横发达的现代社会,身边总会看到看到许多躺读、站读等等姿势各有不同的人,只不过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手中把玩的就是手机,手指不停滑动的是抖音、快手、网游之类的APP;即使读的电子书更多的也只是快餐文化类的家长里短类八卦娱乐资讯;节奏飞快的喧闹都市,已经鲜有人能静下心来,找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来伏案捧读。于是,不由得让我更加怀念那养分流失的鎏金读书岁月,那个承载了我那年少轻狂的方寸之间的书屋,因为梦想而漫长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对未来、对我的家、我的国有了美好的张望。
初中到高中时,我最喜欢跑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从最早办了一本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一本到为了免除奔跑之苦办了两本借书证,和图书管理员熟络后,每次到图书馆总在管理员的默许下抱回一大摞图书。而且一般还书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天,借到的书有损坏的总要小心翼翼地修复了再归还。我现在也很诧异当时的自己,当时借书来读的疯狂模式,课堂上偷读、被窝里躲读、同学间借读、厕所里蹲读……最喜欢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的浪漫逍遥、遐思缥缈,武侠小说的侠肝义胆、铁骨柔情;更喜欢文学名著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心有正气天地宽的交流与碰撞。会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心底圣洁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精神复苏和道德升华崇高悲怆的冉·阿让的多粲际遇而喟叹不已;也会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平民百姓的国家大义、草莽英雄的江湖义气而仰天长啸,而今细细看来,在任何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不遵守法纪的江湖义气绝不会被允许,虽然从个人感情和道义来说,“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有值得推崇之处,但是在人情世故、国家大义面前,洞若观火比较而言,桃园结义般为远大志向而共同努力的家国情义,才值得尊崇,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众志成城铸就伟大复兴之梦正所需要的。
多年前,我的书屋就是一间简陋的卧室,但最醒目的就是床边书柜上堆满的七零八落的书籍,也是我引以为傲的。那时家中经济不大宽裕,书价又特别昂贵,动辄十来块甚至几十块,买书可以说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情。所以兜里一旦有点零花钱,就会省下到书店去买上本把心仪已久的书;倘若钱只有几毛或几块钱的话,就会留到赶集时到旧书摊淘上一两本,大快朵颐。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的苦楚。“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这种经历对于生活在温室里的孩子简直不可想象。尤需倍加珍惜。
现在,我的书屋依旧是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书柜上依然堆满各类厚薄不均的各类书籍。就像妻一针见血说的:你这是装点读书人所谓的清高。我哑然,无言以对。的确,现在的我到书柜翻书、找书、看书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但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偶尔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同时,不经意回眸“那书却在灯火阑珊处”,呵呵,居然能偷闲享受这份安宁,有一段真正属于自己与书独处居家的幸福时光。确实美哉!
最喜欢的是能拥有刘禹锡的《陋室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书屋,如“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般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清静雅致;最窃喜的是莫泊桑笔下《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神交畅聊;最憧憬的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鸡犬之声相闻”,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世外桃源。或许,泡一杯酽茶,执一本闲书,信手拈读,在时光书屋的濡染下,身心投入的过程,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让自己的心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镇静下来,沉淀,反思,观察,吸纳,让自己可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改变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当然,这是狭义方面的自我陶醉的读书,“小我”似的“小家”读书情怀。
培根说:“读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倘若说广义方面的读书,就是改变小我立身家国命运的道理和逻辑。这才是读书的真正价值所在,既能打破自己固化的思维局限,更能提升我们的认知。孙中山先生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就不能够生活。”学会看透自己,体谅他人,理解时代环境,才能更好地与人合作,实现共赢。俯仰古今、学而深思。周恩来总理从小学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南开学校毕业时与同学们互赠“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留言至今仍然振聋发聩。他少年定下初心,之后为之奋斗终身,矢志不渝,践行了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执着的人生追求,为后人所景仰。
放眼神州大地,书香氛围愈发浓厚,精神之花繁茂芬芳。时不我待,读书源自内心的欢喜,在中华民族这饱经沧桑历练的承载五千年文明渊源的大书上,尤需我辈自强不息砥砺前行,践行续写民族复兴初心使命的伟大篇章。为中国之富强而读书。这才是当下我辈赓续精神血脉所应该读的,必须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