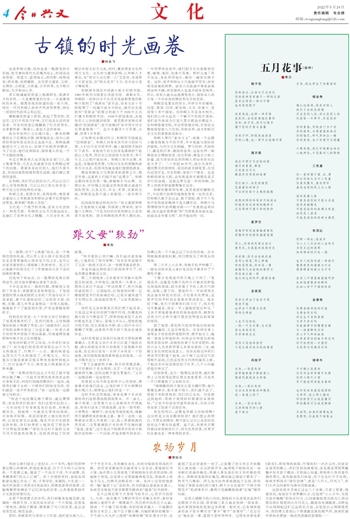■何永飞
走进和顺古镇,犹如走进一幅静美的水彩画,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嘎然而止,时间在这里停留。那蓝天,蓝得纯正;那田野,绿得动容;那水塘,亮得耀眼。还有那古建筑、古树、古牌坊、古祠堂、古街道、古石桥等,无不吸引眼球,无不牵动心灵。
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落满阳光,落满岁月的音符,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一头连着美好的未来。错落有致的街道织成一张大网,网住一代代和顺人的欢声笑语和梦想,网住一团团时代的风云和记忆。
懒散睡在街道上的狗,收起了警觉性,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守护神,它们也是生活的享受者。所有的敌意已被翻到了时光的背后,来者都怀着一颗善心,谁也不会伤害谁。
洗衣亭依然伫立在渡口处,一群身材婀娜的女子在漂洗衣服,赃物能洗去,而内心的那份牵挂和思念却怎么也洗不去。阵阵涟漪能锁住天上的白云,却锁不住郎君的脚步。为了生活,他们走南闯北,留给爱人的是一个个无眠的夜晚。
年近古稀的老人安详地坐在家门口,脸上堆着笑容,可怎么也遮盖不住光阴踏过留下的沟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们不喜不悲,世间的离愁别绪和得失成败,他们都已看得很透彻。
在和顺,我们可以找回自己,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栖息,可以让自己的生命享受一种天伦之乐和纯粹的幸福。
和顺之美,美得自然,美得独特,难怪著名爱国人士李根源来和顺后会情不自禁地吟诗赞美,称和顺“绝胜小苏杭”。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没有文化会给人一种荒芜感。和顺的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还融汇了各种文化之精髓。六百余年来,和顺以中原文化为主流,同时,兼容南亚文化和西方文化。文化的力量和影响,让和顺人才辈出,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有翡翠大王张宝廷,有“桥头老爷”寸玉,有辛亥元老寸尊福等。
和顺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1980年被列为国家公共图书馆。清朝末年,和顺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戊戌变法新思想的影响下组织了“咸新社”读书会,后来又在十字街租用了一间铺子成为书报社,最后在先进组织“崇新会”的鼎立相助下于1928年正式扩建为和顺图书馆。1938年新馆落成,各地知名人士纷纷题词祝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题词“民智源泉”,张天放题词“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迄今有藏书7万多册,古籍、珍本1万多册。
正如熊庆来题词所言,和顺图书馆就是“民智源泉”。和顺人向来有读书学习的好习惯,人们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就到图书馆的灯下读书。有些放牛的人经常是清晨把牛赶到山上吃草,然后自己回到图书馆看书,等下午又上山把牛赶回来。和顺人知书达理,有远见,有超前的思想,与知识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不无关系,而图书馆就是他们智慧的源泉。
都说和顺是大马帮驮来的翡翠之乡,数百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开始“走夷方”。和顺是面向南亚的第一镇,离缅甸才70公里。长期以来,中印缅之间通过西南丝绸古道进行国际贸易,以及文化、外交、军事、宗教的交流,和顺是这条古道上的枢纽,一直非常兴旺。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诗句:“有女莫嫁和顺乡,才是新娘又成孀,异国黄土埋骨肉,家中巷口立牌坊。”可见当时的有些和顺女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和顺的很多男人都经商,一年四季奔走在外,他们把玉石生意做到印度、缅甸、美国、加拿大等地。那时交通工具不发达,身在异国他乡,要回一趟家实属不易。这样,很多和顺女人只能独守空房,夜夜承受寂寞的煎熬。还有人在旅途中难免会遇到各种不测,再坚强的人也逃不脱生老病死,所以,有些人就永远地埋骨他乡,留给亲人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牌坊和无尽的悲伤。
和顺还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分布在缅甸、印度、泰国、印尼、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十多个国家。但和顺人不管身在何方,他们的心中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故乡情结。他们在外面成为巨富大贾后都会衣锦还乡,在和顺修建宅院,并出资修建宗祠,目前还完整地保留着八大宗祠,风格各异,成为和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顺人奉行“拿来主义”,致使一个边陲小镇变得极为不同寻常,早早地就与国际经济接轨,与西方文化相融。罗马的钟、英国的门、捷克的灯罩、德国的盆等,这些东西一般都要放在博物馆里,而在和顺,都是在大街上扔着,因为类似的东西和顺人带回来的实在是太多了。二十世纪40年代,高尔夫球杆、德国蔡司的照相机、美国的派克钢笔等,在国内还很罕见,可在和顺,家家户户都有。走进和顺的深宅大院,会发现连泔水桶都是美孚洋行的油桶。这就是聚宝盆一样的和顺,世界上的很多财富都聚集在这里。
和顺的繁荣和发展,及其获得的耀眼光芒,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一定的关系,但和顺人敢于走出去、敢于冒险、敢于天下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才是关键所在。和顺大马帮博物馆外的两幅对联——“负重致远南丝路,流光溢彩翡翠城”和“马帮载来朱波友谊,商旅送去华夏文明”,似乎能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