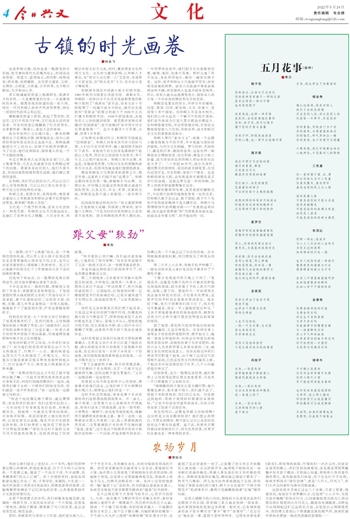■李仙云
我的父辈们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用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地处秦直道、位于子午岭大山深处的一个荒僻之地,建成了一个良田千顷、牛羊成群、瓜果飘香的“陕北小江南”。我十岁到那里时,农场各项配套设施已齐全,厂部、子弟学校、家属院、大礼堂……每次听到郭兰英那首《南泥湾》,那激情澎拜的旋律,总能唤醒那些栖息于记忆深处的往事,让我重温那段年少无忧的妙曼时光。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却像身处桃花源,家属院一排排平房,大家犹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经常是一家炖肉,满院子飘香,哪家做了可口的饭菜,也总会邻里互送,相互品尝。
那时,我极喜欢与邻居小兰玩耍,他们家兄妹八人,个个才艺不凡,有的擅长音乐,有的对绘画有很高的天赋。我经常安静地待在她哥哥小宝身边,看他画牡丹大象,每次看小宝哥画笔下那栩栩如生的花草动物,我就眸子发亮,总觉得小宝哥就像神笔马良,那画纸上的兔子马儿,仿佛灵动鲜活的一样。有次小宝哥把他画的一幅“猛虎下山”送给我,我当即就让爸爸挂在墙上,如获至宝般每天放学都要先跟我的“猛虎”打声招呼。
至今记得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心灵手巧的萍儿,与我一起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采集玉米杆,拿回家她细心地将外皮一缕缕剥开,然后将中间的芯子压扁,剪成一个个瘪了的花瓣,再轻轻将其插入一个扁圆好看的玉米芯上,每个芯子插五瓣,当她把做好的模型一个个浸入在火炉上烧得“咕嘟咕嘟”的红墨水汁时,也就到了见证奇迹的一刻了,之前瘪了的玉米芯开始像花儿绽放般一点点舒展开来,她用筷子轻轻夹出一朵朵鲜红欲滴的梅花,再插入事先备好的玉米杆做的枝条上,那鲜亮美艳的红梅花,瞬间就让满屋子都有了一种灵气与雅韵。萍儿也无比欣喜地翘起兰花指,给我唱起了秦腔名段《虎口缘》,两个少女在窗外“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寒冬日,像两只花蝴蝶般绕着“红梅”嬉笑玩闹。
在那人烟稀少的山沟沟,傍晚的大礼堂简直是我们这群孩子的乐园,那里隔三差五就会放映一部电影。每次看到放映机投射过来那雾一般的光,总有调皮捣蛋的孩子张牙舞爪在“雾中”像个“表情帝”,“丑态百出”地乱扭一番,惹得大家哄笑呵斥。记得有次看电影《画皮》,那惊悚的画面,吓得我们一次次尖叫,回家走在漆黑的路上,我们互相肩搂着肩,还是感觉周围黑魆魆中似有影子蠕动,正胆战心惊着,那些胆大喜欢恶作剧的男生,竟然跑到我们面前,在下巴处打开手电筒,暗夜里那面目“狰狞恐怖”,真是“人吓人,吓死人”,我们大声尖叫着作鸟兽状四散逃离。
这段农场岁月虽已过去三十余载,可黄土厚重,情感深沉,每每在午夜梦醒时分,忆起那“小小少年,无忧无虑乐陶陶”的快乐时光,心间就像绽放在陕北山茆沟壑间那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儿,靓丽而充满暖意,耳畔也不由得响起空旷辽远的信天游,在悠悠白云绵绵情思中,我仿佛又看到山下那清澈见底的葫芦河,袅袅炊烟中那如水墨画一般淡然清幽的家属院……